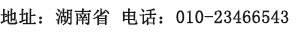三阴性乳腺癌是所有乳腺癌中最难治的一种,因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三个主要标志物均为阴性而被称为“三阴”,约占整体乳腺癌的15%,由于缺乏治疗靶点、复发转移风险高,而成为乳腺癌治疗领域长期以来难以攻克的“堡垒”。
日前,医院乳腺外科邵志敏教授、王中华教授团队的系列研究成果证实,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有望从精准免疫治疗中获益,客观缓解率远高于既往单纯化疗的治疗方案;其中,晚期免疫调节型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客观缓解率可达81.3%,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延长至13.6个月,为当前晚期三阴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最高数据。
在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进行口头汇报后,国际肿瘤领域学术期刊《临床癌症研究》(ClinicalCancerResearch,影响因子12.5分)、《分子癌症》(MolecularCancer,影响因子27.4分)于近日先后刊发了该系列研究的临床试验和转化分析结果。
基于前期研究的深入探索,为临床联合用药提供新思路
早在年,邵志敏教授领衔团队绘制出了全球最大的三阴性乳腺癌多组学图谱,证实三阴性乳腺癌并不是一种单一类型的疾病,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三阴性乳腺癌“复旦分型”,将三阴性乳腺癌分为4个不同的亚型:免疫调节型、腔面雄激素受体型、基底样免疫抑制型和间质型,为寻找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靶点指明了方向。
基于精准的分型方法,邵志敏教授和王中华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名为“FUTURE(未来)”的“伞形”研究,根据“复旦分型”的精准分类及潜在治疗靶点,指导相应的精准治疗,为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有的放矢”地选用合适的治疗方案。
免疫调节型是三阴性乳腺癌“复旦分型”中的一种,此类乳腺癌细胞周围有大量淋巴细胞,这意味着此类亚型可能对免疫治疗敏感。在FUTURE研究的C臂中,研究团队发现归类为免疫调节型的难治性三阴性乳腺癌患者,通过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方法,有52.6%的患者获得客观缓解,病情得到良好控制,这一数据远高于既往接受化疗的患者。
是什么导致了疗效的明显差异?基于这一发现,研究团队进一步针对免疫调节型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开展深入研究。
通过基因检测技术和大数据的比对分析,邵志敏教授团队发现,在免疫调节型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CD8评分能够有效区分“冷、热肿瘤”,且其中免疫活性分子表达与肿瘤血管生成信号呈现高度负相关。
动物实验证实,抗血管生成小分子药物法米替尼增加了CD8+T细胞的浸润和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的表达,该药物联合免疫治疗和化疗可以更有效地抑制三阴性乳腺癌生长。
这为临床上联合使用抗血管生成药物、免疫治疗药物以及化疗药物治疗免疫调节型三阴性乳腺癌提供了新思路。
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为三阴乳腺癌患者带来新希望
基于前期研究发现,研究团队将FUTURE-C臂的方案推进至一线治疗,开展了名为FUTURE-C-Plus的临床试验。
该试验共纳入了48例初诊为局部进展或复发转移性的免疫调节型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予以抗血管生成小分子药物法米替尼联合免疫治疗药物卡瑞利珠单抗+化疗药物白蛋白紫杉醇方案进行治疗。
数据显示,治疗组患者总体客观缓解率进一步提升至81.3%,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延长至13.6个月,达到目前已知三阴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最高客观缓解率,为免疫调节型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有效治疗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给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带来全新希望。邵志敏教授受邀在年ASCO年会对该项研究成果进行口头报告。
在FUTURE-C-Plus研究中,研究团队不断发现“新大陆”。肿瘤PKD1基因体细胞突变提示患者不良疗效,CD8结合PD-L1评分有望成为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免疫治疗更为合适的临床标志物,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后续研究验证。
“这两项延续性的研究成果,为改善难治性三阴性乳腺癌的疗效提供了新思路,让精准免疫治疗成为了可能,”邵志敏教授表示,“此外,系列研究也实现‘临床问题-基础研究-临床转化’的全链条闭环。通过高通量解析肿瘤微环境、多维度鉴定免疫逃逸关键机制、广覆盖开展精准治疗临床试验,有望奠定未来三阴性乳腺癌的精准免疫治疗新格局。”
通讯员医院吴松阳王广兆
中国医学论坛报刘佳玲整理
中国医学论坛报将每周定期推送肿瘤领域最新进展,传递专家观点,分享学术共识,一起来看吧!
还可扫码